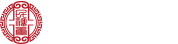男欢女爱里 到底谁消遣了谁
我是你名单中的一个
主人公:徐平34岁财务总监
认识皑皑的时候,我承认我是去猎色的。在震耳欲聋的舞曲声中,喝得微醺的男男女女形态各异地摇摆,空气中的气味很繁杂,有种很简单直白的快乐。我就和皑皑坐在吧台边,大着嗓子说话,大口大口地喝酒。
皑皑并不是很漂亮的女孩子,即使在迪吧并不明亮的光中也能看出她长相的某些缺陷,可是,皑皑却是一个非常媚惑的女孩子,一股子独有的媚态从骨子里泛出来,让人觉得非常渴望。早些时候,清朝的花花公子李渔不是说过吗,“女子一有媚态,三四分姿色,便可抵过七八分”。所以,在我眼里,皑皑是那么的美。
喝到七八分的时候,我们去了宾馆。像一株常青藤似的皑皑缠绕着我,她指着我的鼻子,用迷离的眼神看着我,然后说:“告诉你,你不可以爱上我哦!”
可一夜缠绵后,我却喜欢上了她。不光是她年轻的身体,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。女子的妩媚常常是这样,宛如行走在一团浓雾里,一直想辨清前面的路,可是兜兜转转却越发迷糊。本来,像我这样离过婚的男人,不应该这么没有定力,可是于她,一切的规则似乎都显得太过于迂腐。
我说,皑皑,做我的女朋友,跟我一起生活好吗?皑皑就惋惜地看着我,你有钱、有品位、有长相,为什么偏爱我这样的露水情缘呢?我不是告诉过你吗?你不可以爱上我哦,你忘了吗?
这样说的时候,她却已经纠缠过来,仿佛那只是如电影里的开场白。所谓颠倒众生,也不过如此吧。
我相信,我能拴住她,即使她是暴躁的枣红马!
我抽许多时间放在她身上,变着法子想讨她欢心,给她买礼物,她的一句话就能成为我的圣旨,我甚至愿意在她那里迷失了我自己,只要她温柔,妩媚地呆在我的身边。不过这些并没有能够让她有什么变化,她对我并不冷淡,某些时候,她甚至主动要求我的温存。可是她也从来不把我当归属,很多时候,我都打不通她的电话。她独享着她秘密的快乐,而把我置于冰火两重天下——当然,这都是我自找的。
当我知道,如我这样的人,在她的名单里不止一个的时候,我先是震惊,再是伤痛,后一片空茫了,不过第二天,我就哑然而笑了,多么愚蠢的人啦,居然忘了自己的初衷,不就是一场猎色行动吗?
偶尔,会约着出来,温一下斑驳迤逦的旧梦。她依然是老样子,不多给你一分,也不少你一毫。也曾在街头偶遇,牵着另外一个男人的手,坦然到有些无耻。她是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,“我请客,你埋单。”大家来一场情与欲的盛宴而已。
曾经有一篇文章,说这样的女人是有毒的,她们就像罂粟,经历了一个花期后,“会变得更加媚惑,每一段的情感经历于她只是吸引力的新源泉。她懂得爱也要求爱,她让那些男人上了瘾,明知道这快乐是有毒的,也一次次带着下不为例的心上路”,不知道下一个中毒的人会是谁?
从以上的爱情宝典中,我们可以体会到那句“女人是毒药”话中的含义。的确,女人的美就像是罂粟,经过一个有一个的花期,都可以不断地吸引人为之向往,而中毒的人却在不停更换。
女人观点:质不够就有了量
那天和几个同是单身的女友在后海消遣。
时间过得快,后我们几个自由的女人决定玩一会儿“老实说”的游戏就散去,“你第一次被男人伤害是什么时候?”小青问我。“四岁的时候,爸爸死活不给我买小白兔玩。”我奸猾地躲过了敏感问题。“你现在有没有可睡的男人?”我问目前无男友的咪咪。“当然有了,不然还能有精神出来混?”咪咪答得痛快,之后转过头问芳芳:“你睡过多少个呀?”“呵呵!”芳芳一笑,“三十个算什么来的?”“三十到五十是过于开放。”我答之。“哦,好像没那么多,我得回家拿纸笔好好算算,现在不好说。”“呸!你这个不老实的东西。”咪咪举手就打。“你这虐待狂女人,又欺负我。”芳芳表情那么无辜,透出一种日积月累的妩媚,或许真像她说的那样,女人修炼成妖精,绝对是要在男人们身上实现的,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纯洁的女妖。咪咪却说值不值不在于人数,完全是质量决定的。一个男人能不断满足一个女人的欲望和情感,那她还要别的男人干嘛?现在很多女人的困惑主要是在于能令人满足的男人太少了。也是,现在这都市男女们似乎性别的差异逐渐模糊起来,男人嫌女人越来越随便,个个都是花心,开放的单身女人则认为由于男人越来越感性而随波逐流,才使天长地久听起来像神话,而她们只能游走在一个接一个的男人中间,去寻找不知何时出现的真命天子,因此多尝了几个男人的滋味,也算不得是赚了什么便宜吧。